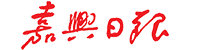■记者 蔡舒安 陈 曦
通讯员 汪燕鸣 王佳萱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插画 张利昌
【撇出故事】
昨天上午,南湖区湘家荡桥埭老街上,一间名为“缘髹轩”的漆器工作室内静悄悄的。
袁茂才坐在工作台前,正要给一个木瓶上第一遍漆,他手边是事前调制好的绿松石大漆,加少量松节油稀释,搅拌均匀后,袁茂才拿发刷蘸取,小心地进行涂刷。
大漆凝重而绚烂、含蓄又热烈,每一件作品都极具东方气韵。去年11月,沉寂3年的李子柒带着一件名为“紫气东来”的漆艺作品重归大众视野。一时间,很多人知道了大漆,并开始关注这门古老的传统技艺。
今年46岁的袁茂才,从少年时代便开始了和漆艺的“不了情”,多件作品摘得全国大奖。“缠绵”30余年,袁茂才自己也成长为第三批嘉兴市南湖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大漆髹饰”代表性传承人、嘉兴市级乡村工匠。
“不管怎么样都给我扛着”
“我叔叔就是做大漆工作的,从小我便看着他做,渐渐就对这个工艺产生了兴趣。”袁茂才与大漆的缘分,源于他的少年时期。
这种兴趣,像一颗种子,在袁茂才心田生根发芽。
1992年,袁茂才早早离开家乡,从四川南充只身到宁波拜师学艺,正式开始学习大漆工艺。
大漆是一种天然树脂涂料。割开漆树树皮,从韧皮内会流出一种白色黏性乳液,再经过加工制成的涂料就是大漆。别看它是一种纯天然的产品,却是一种非常容易导致人过敏的原料,即使穿上长袖长裤也无法阻挡,严重时,人哪怕只是在漆树下经过都有可能过敏。
初学时,袁茂才也没少“受罪”。第一次接触大漆后,手、手臂、脸……裸露在外的皮肤几乎全部起了疹子,又红又痒,眼睛更是肿得只能睁开一条缝,“我当时马上就不想学了,哭着喊着要写信给父亲,让他接我回家。”
信从宁波寄回四川的路程十分漫长。起初,身上又红又肿的袁茂才啥也干不了,天天眼巴巴地等着父亲的回信。渐渐地,他的目光被大漆吸引了,又跟着师父学起了大漆。等父亲的回信送到,袁茂才身上的过敏症状也已经消失了。
和袁茂才一起学习技艺的共有6人,师父一边带着他们给红木家具做大漆,一边传授大漆技艺。这其中,袁茂才是天赋最高的一个,学到第8个月他就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他白天跟着师父制作红木家具,给家具上漆。晚上回来就在自己宿舍琢磨,做出来了就向师父请教,一点点改进。仅两年左右的时间,他就把大漆技艺基本学会了,从师父的徒弟变成帮助师父带徒弟的助手。师父常常说他悟性高,夸赞袁茂才是他的骄傲!
出师之后,袁茂才继续给红木家具的厂子做大漆,最多的时候,他兼了7个厂子的家具刷漆工作,每天能赚2万多块钱,那可是一笔了不得的数目。
2016年,袁茂才借一次修理家具的契机,从宁波来到了嘉兴湘家荡。来到新的环境,袁茂才也有了新的想法:“我想全心做大漆。”不顾身边人的反对,袁茂才放弃了年收入近20万元的工作,在城南的一个公寓里租了间房子,一股脑“扎”进了大漆技艺中,“别说家里人了,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反对我这样做,话都说得特别伤人,我现在想起来都会鼻子酸。”袁茂才的一个朋友曾对他说:“做这个东西,你能坚持一年我就服你……”
没想到,他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很多时候,做大漆投入和回报不成正比。初到嘉兴,袁茂才光吃青菜面条就吃了半年,唯独对大漆特别舍得花钱。漆这一原材料每公斤的价格在千元左右。为了保证作品的呈现效果,他选的工具也都不便宜,用来刷灰的刷子,一把也要好几百元。问及原因,袁茂才脱口而出:“我就是喜欢做大漆。”
袁茂才还记得那封年少时跋涉千里的信,信上是父亲坚定的笔迹,没有过多言语,只有一句“不管怎么样都给我扛着,不许回家!”说来也巧,大部分人接触大漆后都很难脱敏,袁茂才过敏了那一回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发作情况,他觉得,“这可能是我和大漆天生的缘分。”
“我就是跟漆‘造’了一辈子”
去袁茂才的漆器工作室,迎接客人的是摆了整整一屋子的漆器作品,从茶杯到花瓶,从乐器到围炉煮茶器具,从画舫到古琴,袁茂才的作品种类繁多,约1700件。
再往里走,内部的工作台才是袁茂才待得最多的地方。左手捏着一只小茶杯,右手握着一根蘸满浓漆的小木棍,他正小心翼翼地将浓漆点涂到杯身上。他介绍,不能涂得太均匀,而是要有厚有薄,再一遍遍给它上底漆,要上40多遍才能填满。在工作台前一坐,打开手机播放几首老歌,他在这里能坐上一整天。
2020年冬季,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在温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当时展厅里一个高挑美丽的花瓶引来观众阵阵惊叹。
这款有着不同颜色花纹的花瓶,正是出自袁茂才之手,也是他的得意之作。“这个作品是我在‘吃青菜面条’那段时间里做出来的,你看,瓶身上有很多色彩,作品名就叫‘五彩嘉兴’。”这件作品获得了当年“快鹿杯”工艺美术创新设计大奖赛金奖。
“五彩嘉兴”采用的工艺叫脱胎,也称为布胎,是最古老最传统的做法。这种工艺就是从捏泥巴开始,先拉好一个坯。这是制作过程中的一大挑战,需要将泥巴形状塑造得当,达到一定的硬度后打磨至光滑,之后才能在泥巴上面刷漆。袁茂才记得,这件作品他反复刷漆160道,每一层都要自然干透才能进入下一道工序。
袁茂才的工作室有一个专门用来晾漆的房间,里面挂满了温湿度计。每天,袁茂才都要调整房间里的温度和湿度,让每一层漆的效果达到完美。房间角落里,几台已经用废的加湿器堆叠在一起,见证着袁茂才对大漆工艺的精益求精。“天气、含水量都会影响色漆的流淌,因此器物上的纹理无法预判。”袁茂才觉得这一过程就像开盲盒,不到最后一天,你永远想象不到它能美成什么样。
“这样复杂的工序下来,成品一定很重吧?”记者上手掂量了一下,居然非常轻盈。轻的同时却十分牢固,试着摔打几下,整个花瓶没有任何变化。这是怎么做到的?袁茂才指着花瓶内部介绍,整件作品就是漆组成的,晒干定型之后还有一步脱坯,需要将花瓶中间用于塑形的泥巴坯脱出来,这是一道非常难的工序,“要保证不能变形,也不能影响硬度,上面有纹路也要完整地脱出来。”有人曾经为这件作品开价48000元,袁茂才坚决不卖。
做大漆,必须耐得住性子。固胎、挂灰、粗坯打磨、刷底漆、重复涂漆、水磨……制作一件大漆作品,每一个步骤都极尽繁复,一件普通的工艺品也要经过几十道甚至上百道工序,需要丰富的经验和恒久的耐心,才能成就一个时间与手工相融合的“奢侈品”。
在当今快节奏的社会,漆艺的路在哪里?
袁茂才觉得,有着7000多年历史的“国漆”既要传承,也要创新。曾经用泥土做茶杯模具,内部脱模的方式导致茶杯的底部总是大小不一,袁茂才为此研发了外部脱模的方式,确保了所做杯型的统一;犀皮纹理无法满足大众需求,袁茂才就自己设计了大块的鎏金纹理。
多年来,袁茂才也在不断地寻求大漆与其他艺术形式的统一。在他店内,放着一个“镇店之宝”——大漆画舫。这艘船,也是2023嘉兴文化产业博览会上南湖馆的“镇馆之宝”。全船256个配件,逐个采用了起皱、红金斑、描金等10多种大漆技法工艺进行髹饰,流光溢彩,让整艘画舫变得极其华贵。
大漆这种材料,只有东方才有,一棵漆树一年只能产半斤左右大漆,弥足珍贵。袁茂才说自己是为漆生、为漆死,跟漆“造”了一辈子。看着满屋子的大漆作品,他发自内心感到充盈。
“能做自己最热爱的事,我很幸运!”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大漆吗?”每周三下午,袁茂才在七星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有两节木工课,不大的教室里聚集着12个学生。即使只分辨得出黑绿红金数种颜色,但器物却呈现出斑斓万象、流光溢彩的质感,第一次见到大漆工艺的学生都会被这种美深深震撼。
第一堂课,袁茂才只要有条件,就会带着学生们领略一遍大漆的制作工艺。通过捏泥巴体验大漆制坯,借助剪纸感受设计花纹,通过亲手制作漆扇初步实践大漆技艺……一堂课下来,学生们已经有些疲惫。看似简单的练习,却是练就扎实基本功的关键。在袁茂才看来,这些繁复的工序是漆艺的灵魂,而且这些步骤没有捷径,只能依靠日积月累的经验。
放在以前,一件好的大漆作品,光靠一个人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它需要一个好的木工、一个好的漆工,还需要一个书法家或者画家。“以前做大漆的人还需要一定的美术功底,现在有了电脑打印之后反而不需要了。”但袁茂才坚持亲手完成每一个步骤,即便是看上去毫无含金量的打磨,也是决定作品美感的关键步骤。他认为这是制作者手、脑、心和谐统一的展现,绝不能被工业化取代。
很多初学者因为掌握不好打磨的力度和程度,常常功亏一篑。袁茂才自己也会因为不满意作品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放弃辛辛苦苦好几年的心血,重新做一个作品,“我身边朋友都说这样已经很好了,但我自己觉得不满意就要重做。”
这些年,愿意来学习手艺的年轻人不少,上手也不难。难的是沉下心来做并坚持下去,“想要做出一件像样的作品,少则3个月,多则好几年。”对于急于想看到结果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时间“沉没成本”有些太高了。袁茂才也说,寂寞是初学者最难过的一关。
“时至如今,大漆仍然是一种很冷门的技艺。”袁茂才说起曾有人把大漆的茶杯当作塑料制品的经历,脸上有些落寞。为了让漆器更贴近大众生活,袁茂才也从大众的需求中看到了新的创作方向,创作了好几件围炉煮茶的茶具。精美的纹理、雅致的形态和干净的质感,成为冬日三五好友小聚的雅致享受。
现在,袁茂才也在试水抖音直播,希望将大漆技艺传播给更多人,在一些文创市集上,也能看到袁茂才的身影和作品。他觉得只有通过不断宣传和推广,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大漆,这门古老的技艺才能走得更远、更久。
值得庆幸的是,大漆在袁茂才手中一次次释放出生命力,他也将自己的生命力嵌入漆艺之中。他说:“能做自己最热爱的事,我很幸运!”
【捺出态度】
一间工作室,一个人,是袁茂才的日常。
因为大漆还具有耐酸碱、抗腐蚀、防静电等多重作用,在中国历史上,髹饰技艺曾一度达到“无物不髹”的繁盛之境。在袁茂才的工作室我们看到,大到家具礼器,小到饰品茶具,统统在大漆的包裹下焕发新生。
从了解漆的产生、制作方法,到可以练习独立完成一个简单作品,再慢慢过渡到将简单的漆器描绘出层次及色彩,将它以最完美的形式展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袁茂才愈发体会到大漆的魅力,手艺也日渐成熟。在袁茂才的世界里,大漆不仅是一种涂料、一种工艺,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他用双手和匠心,将这门传统技艺传承下去,并赋予新的生命。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作为非遗大省,今年,浙江省对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作出系列重大部署,嘉兴也提出要传承弘扬“两个文化”,建设高水平文化强市。
只有深深扎根土壤,才能收获繁花绚烂。令袁茂才感到欣慰的是,大漆技艺已经被越来越多人熟知,“大漆的魅力在于它能包容万物,我也希望能有更多人认识、了解这门古老技艺,让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不只是大漆技艺,对于非遗技艺来说,最好的传承是让其发光发亮。
从一方工作室,到更广阔的舞台,袁茂才还在不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