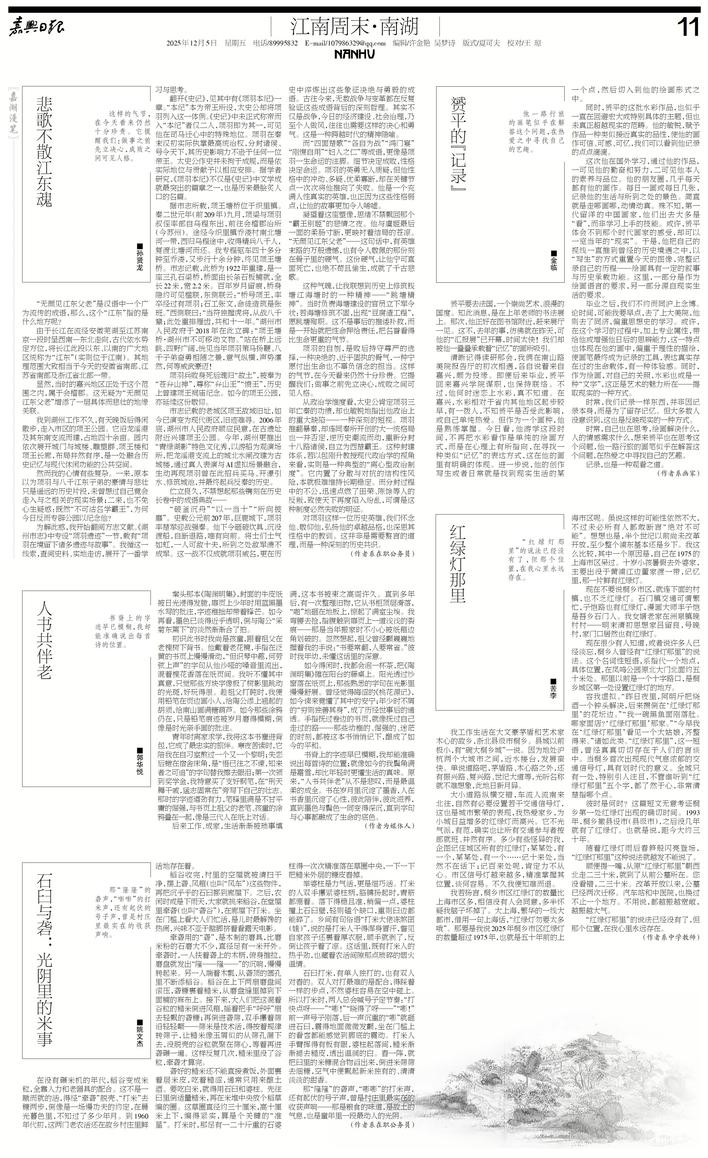■姚文杰
在没有碾米机的年代,稻谷变成米粒,全靠人力和老器具的配合。这不是一蹴而就的活,得经“牵砻”脱壳、“打米”去糠两步,倒像是一场慢功夫的约定,在晨光暮色里,不知过了多少年月。到1960年代初,这两门老农活还在故乡村庄里鲜活地存在着。
稻谷收完,村里的空屋就被清扫干净,摆上砻、风箱(也叫“风车”)这些物件,再把沉乎乎的石臼挪到廊屋下。之后,农闲时或是下雨天,大家就挑来稻谷,在堂屋里牵砻(也叫“砻谷”),在廊屋下打米。坐在门槛上看大人们忙活,是儿时最解馋的热闹,兴味不亚于踮脚挤着看露天电影。
牵砻用的“砻”,是木制的磨具,比磨米粉的石磨大不少,直径足有一米开外。牵砻时,一人扶着砻上的木柄,俯身推拉,磨盘就发出“隆——隆——”的沉响,慢慢转起来。另一人端着木瓢,从砻顶的圆孔里不断添稻谷。稻谷在上下两扇磨盘间滚压,砻糠裹着糙米,从磨盘缝里掉到下面铺的麻布上。接下来,大人们把这混着谷粒的糙米倒进风箱,摇着把手“呼呼”扇去轻飘的砻糠;再倒进砻筛,双手攥着筛沿轻轻颠——筛米是技术活,得按着规律转筛子,让糙米像玉屑似的从筛孔漏下去,没脱壳的谷粒就聚在筛心,等着再进砻碾一遍。这样反复几次,糙米里没了谷粒,牵砻才算完。
砻好的糙米还不能直接煮饭,外面裹着层米皮,吃着糙涩,通常只用来酿土酒。要吃白米,就得用石臼和婆柱。先往臼里倒适量糙米,再在米堆中央放个稻草编的圈。这草圈直径约三十厘米,高十厘米上下,编得紧实,算是个关键的“准星”。打米时,那足有一二十斤重的石婆柱得一次次精准落在草圈中央,一下一下把糙米外层的糠皮舂掉。
举婆柱是力气活,更是细巧活。打米的人双手攥紧婆柱柄,胳膊扬起时,青筋都绷着。落下得稳且准,稍偏一点,婆柱撞上石臼壁,轻则磕个缺口,重则臼边都能碎了。乡间有句俗语“打米大佬冻煞囝(娃)”,说的是打米人干得浑身冒汗,瞥见自家孩子还裹着厚衣服,顺手就剥了,反倒让孩子着了凉。这话里,既有打米人的热乎劲,也藏着农活间隙那点琐碎的烟火温情。
石臼打米,有单人独打的,也有双人对舂的。双人对打最难的是配合,得踩着一样的步点,不然婆柱容易在空中碰上。所以打米时,两人总会喊号子定节奏:“打快点呀——”“嘭!”“晓得了呀——”“嘭!”前一声号子刚落,后一声沉重的“嘭”就砸进石臼,震得地面微微发颤,坐在门槛上的看客都能感觉到脚底的震动。打米人手臂挥得有板有眼,婆柱起落间,糙米渐渐褪去糙皮,透出温润的白。舂一阵,就把臼里的米糠混合物舀出来,倒进米筛筛去细糠,空气中便飘起新米独有的、清清淡淡的甜香。
那“隆隆”的砻声,“嘭嘭”的打米声,还有起伏的号子声,曾是村庄里最实在的收获声响——那是粮食的味道,是故土的气息,也是童年里一段最动人的光阴。
(作者系在职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