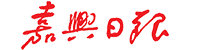■记者 应丽斋 潘琳娟 徐梦倩 沈龑超
插画 张利昌
江南三月,嘉兴市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桃花已悄然破蕾,一场燎原般的盛大绽放近在咫尺。20多年前开通的101路公交车,穿梭于嘉兴与凤桥之间,一头牵着城市的喧嚣和憧憬,一头系着乡村的烂漫与芬芳,见证了城乡流淌的诗意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蓬勃脉动。
对三星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徐利军而言,最近让他应接不暇的是一批又一批前来考察的外地团队。21年前的三月,同样是春暖花开之际,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乘坐101路公交车来到三星村,与乘客、村民亲切交流,仔细询问水蜜桃等农产品的进城销售情况。21年后,这颗曾被总书记牵挂的“致富果”,已成为三星村最闪亮的“IP”,在村党委持续推动的农文旅融合发展中,散发着独特魅力。
三星村与水蜜桃,恰似共生连理、紧密相依,一切似乎顺理成章。但回首过往的半个多世纪,从政策导向到市场环境,再到整体发展大势,三星村桃树能够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夹缝中突围,在市场风起云涌的大潮和工业化、城市化推进的浪潮中屹立不倒,实属不易,靠的是啥?带着上述问题,我们“百村行采访团”来到三星村。
【提问】 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时代,三星桃子如何在夹缝中突围?
三月,踏入嘉兴市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连片桃林便撞入眼帘。朵朵粉色花苞在枝头铆足了劲儿,将积攒一冬的活力凝聚于花瓣间,像是要迫不及待倾泻春天的蓬勃朝气。抬头远望,一幅融合了灼灼桃林、蜿蜒村路与小桥流水人家的长卷徐徐铺展着,尽显江南的灵气与悠然。
记者很是好奇,在计划经济年代,农产品大多实行统购统销,即便是农民在自留地里自产的蔬菜、水果等,政策也只允许“有限制地售卖”。三星村的桃树为何能独辟蹊径悄然生长?
“三星一带种桃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清,但在上世纪70年代,差一点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老书记陆毛娜带领村民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保卫战。”土生土长的徐利军说,1975年5月,嘉兴地委提出要提高对经营管理工作的认识,村集体允许社员在自留地搞家庭副业增加收入这股“歪风”必须刹一刹。
当时的三星村,几乎家家房前屋后都种有桃树。桃子盛产时节,村民会把桃子挑到集镇或者嘉兴城里卖,算是增加家庭收入的重要渠道之一。
1972年出生的徐利军忆起儿时跟着爷爷进城卖桃的情景时,眼里闪着光:“那是我小时候最幸福的事,从村里出发,走上几里的田埂路,到达余新轮船码头,再乘渡船到嘉兴城。就在南湖饭店对面的环城河梧桐树下,我们摆摊吆喝。卖完桃子,爷爷会买一角一碗的馄饨犒劳我,那是乡下孩子馋了一整年的滋味。”
当公社传来要把桃树全部砍掉的消息时,村里顿时炸开了锅。对当时的大队书记陆毛娜来说,最安全最省力的做法是:不折不扣执行公社的指示。但他觉得,工作虽然轻松了,但老百姓心中的怨言滋生了,不利于日后基层工作。他召集党员干部想办法,希望能在既有政策里为桃树找到生存的依据。最后,他以大队党支部的名义担保,向公社立下誓言:“允许三星农民在自留地里保留桃树,保证三星桃子全部以平价销售,不扰乱市场秩序。一旦发现违规现象,以砍掉桃树作为惩戒!”
这一年,桃子上市季节,公社给三星桃子规定的售价是每斤2毛5分。陆毛娜组织民兵连每天到市场上监督巡逻。整整一个夏天,全村只有一户人家心存侥幸,以每斤高出2分的价格出售。当这个桃农从嘉兴城回到村里时,他家的20棵桃树已被砍掉17棵,之所以剩下3棵桃树,是因为陆毛娜的特地叮嘱——“他家有3个孩子,让每个孩子有一棵桃树的指标解解馋”。
就这样,当政策铁臂与乡土伦理相撞时,党组织带头人以一纸镌刻着基层智慧的保证书,将冰冷的行政命令转化为带着地温的契约精神,让桃树在集体承诺下得以合规生存。当发现卖桃子的箩筐逾越制度红线时,村里的主心骨一面以壮士断腕的果决,彰显“徙木立信”的规矩威严;一面以“刀下留树”的收势,传递社会主义大家庭特有的人性关怀。
作为三星村现在的“当家人”,徐利军坦言,老书记“救树”的故事,对他和现在的村两委班子始终是一种教育、一场启迪:村庄治理既不是简单的“理论堆砌”,也不是照本宣科的“一刀切”,而是需要如中医“望闻问切”般,根据具体情况善开良方,让红头文件上的文字在因地制宜中生根发芽,既要长出符合中央精神的枝干,也要结出适配乡土人情的果实。
【追问】 面对市场潮起潮落,三星桃子靠什么脱颖而出?
每一个个体命运的叙事,每一个产业的潮起潮落,都跌宕着时代的澎湃节奏。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落地生根,获得了土地自主经营权的三星农民应阿土率先在自家承包田里试种了2亩桃树。这个大胆尝试很快引发热议:改种经济作物后,公粮任务该如何完成?
应阿土的创举是缘于他对时代发展趋势的把握: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粮食亩产量连年提升。考虑到粮食日渐富足,国家在保障公粮收足的基础上,逐步放开统购统销政策,允许农民在完成定购任务后自主销售余粮。应阿土利用桃园收益,从乡邻手中购买余粮缴纳公粮,而桃子获得的收益,数倍于粮食作物。
这种“以经补农”的创新模式,既守住了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又开辟了增收新渠道。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城里国有企业最高等级的工人八级工为月工资达到100元而欢天喜地时,应阿土大胆采用“鱼塘+葡萄+桃树”立体套种模式,使亩均收益飙升至5000元左右,一时成为轰动十里八乡的明星人物,村民群起而效仿。1988年,三星全村共栽桃树276亩、9660株。
三星村农民以他们特有的务实与智慧,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接壤处,踏出一条充满活力的发展新路。他们中的很多人,或许说不清什么是市场经济,却用田垄间的智慧,将政策文件上的铅字变成了粮仓里的金黄、集市上的喧腾,以及越来越鼓的腰包。
桃树种下去容易,可要让“枝头果”变成“柜上货”,考验接踵而来。
1989年盛夏,三星村桃农进城卖桃遭遇了“拦路虎”:城里戴着红袖章的管理人员以“管理”的名义,追赶得他们无处落脚。“无证摊贩”的标签刺痛着他们的尊严。
“农民卖个桃还要被工商撵,这叫什么事?”村支书张五四代表村民向当时的嘉兴市委书记发问,振聋发聩的拷问直击体制壁垒:“难道社会主义市场容不下社会主义农民?”
村支书为民呼吁,很快得到积极回应。工商局精心印制了“自产自销证”,公安局同步发放“绿色通行证”。一筐筐带着清晨露水的鲜嫩桃子,稳稳占据嘉兴城区农贸市场的显眼位置。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三星桃子的进城故事,原来也深深地镌刻着嘉兴市各级政府部门解放思想为“三农”服务的印记。可是,三星桃子面临的考验总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当葡萄收益远远高于桃子时,桃农们也曾犹豫:是砍掉桃树还是选择坚守?当绿色认证成为消费者眼中品质与健康的象征时,三星的桃产业又该如何踏上逐“绿”之路?
“不能盲目跟风,还是要搞我们自己熟悉的行当。不过,必须创新、必须迭代。”应阿土的儿子应华伦和应华兴继续率领村民以科技破局。智能农机、喷滴灌系统、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让水蜜桃在二三十年间完成一次次品种迭代,从“大团蜜露”到“湖景蜜露”“赤月”等新品种矩阵,实现“论个售”的价值跃迁。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场始于“增产不增收”阵痛的技术革命,将三星村世代耕者的倔强淬炼成现代农业的金色勋章。
三星桃农的突围史,恰似一部镌刻在泥土深处的改革史诗。当陆毛娜以白纸黑字的平价协议为桃树筑起“护城河”,当应阿土用经济作物的根系反哺粮田提高收益,当张五四将村民褶皱的愁眉化作穿透云雾的信笺……我们洞察到,乡村真正意义上的破局突围,源自对脚下这片厚土与生俱来的虔诚敬畏,源自俯身倾听每一个村民心底呼声的诚挚态度,更源自面对艰难险阻时,那永不言弃、坚韧不拔且饱含人性温度的全力守护。
【叩问】 在不断推进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浪潮中,三星桃林未来路在何方?
距嘉兴南站仅8公里的三星村,此刻正站在城乡融合的锋刃之上。工业园区的围墙与桃林防护网近在咫尺,商品楼盘预售广告牌醒目地矗立在观光桃园不远处,此情此景,不禁让人心生疑虑:在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汹涌浪潮中,三星桃林的未来究竟路在何方?
徐利军带我们来到紧邻村委会的旧砖窑,他遥指不远处那座单孔石拱桥,以及矗立在河畔的老水塔,郑重其事地说道:“这些积淀着历史的遗迹,曾见证三星村从农耕文明走向工业时代,如今更要成为桃林存续的守护图腾。即便被‘重重包围’,三星村的桃林也必然会像这些古老遗迹一样,被妥善保留下来。不仅如此,桃林还将以全新的姿态,衍生出与都市发展交相辉映的景观价值。”
在嘉兴城市边界不断外拓的轰鸣声中,三星村已凭借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这一坚实壁垒,为桃林筑牢防护屏障。被高速公路、工业园区、高楼大厦环绕的千亩桃林,不再是被蚕食的“孤岛”,而是化作城市肌理中的“生态芯片”。它既为“钢筋森林”输送着鲜氧与诗意,又以现代科技重构传统农耕的生机:桃花绽放的季节,城市里的家长带着孩子,借助AR导航在三星村沉浸式探寻《桃花源记》的诗词投影;每逢双休日和节假日,城市里那些被“996”工作模式压得喘不过气的人们,会直奔桃林深处的减压营地。在这场城市化、工业化与桃林的博弈中,那些曾经威胁桃林存续的力量,最终都会成为倒逼产业涅槃的推手。徐利军说,如今,三星村的桃树盛景已跨越村界。一群技艺精湛的种桃能手,借技术输出之机,奔赴长三角租地种桃,开启事业新篇。三星村村民坚信,三星桃林的未来,不会在对抗中存续,而是可以在共生中实现新的繁荣。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在嘉禾大地上徐徐铺展,三星村干部无比坚定地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考验,只要传承村里的优良传统——既守得住政策红线,又能把每家每户的难处放在心里捂热;既有向中央看齐、让政策精准落地的政治自觉,又有对人民、土地、未来负责的深厚情怀,那承载着无数希望与梦想的“101共富班车”,必将冲破一切束缚与阻碍,驶向越来越辽阔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