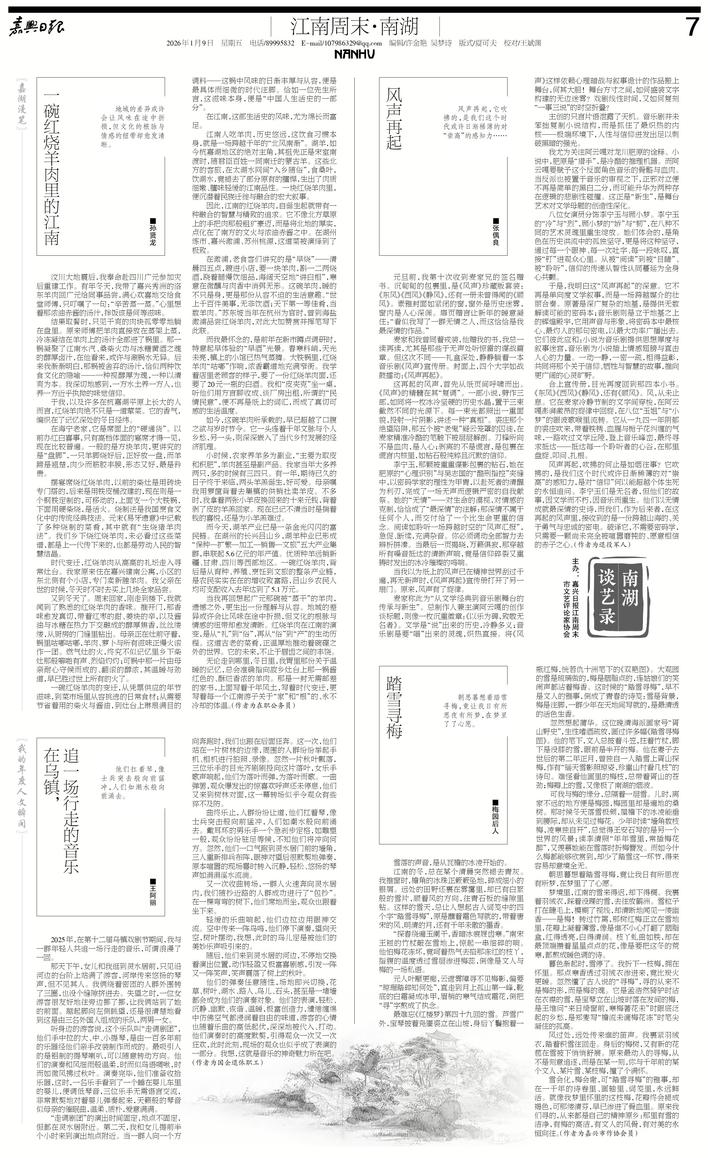■孙贤龙
汶川大地震后,我奉命赴四川广元参加灾后重建工作。有年冬天,我带了嘉兴秀洲的洛东羊肉回广元给同事品尝,满心欢喜地交给食堂师傅,只叮嘱了一句:“辛苦蒸一蒸。”心里想着那浓油赤酱的汤汁,拌饭该是何等滋味。
结果取餐时,只见干爽的肉块孤零零地躺在盘里。原来师傅把羊肉直接放在蒸架上蒸,冷冻凝结在羊肉上的汤汁全部进了锅里。那一锅凝聚了江南水汽、桑柴火功与冰糖黄酒之魂的醇厚卤汁,在他看来,或许与涮锅水无异。后来我渐渐明白,那锅被舍弃的汤汁,恰似两种饮食文化的隐喻——一种视醇厚为魂,一种以清爽为本。我深切地感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方近乎执拗的味觉信仰。
于我,以及许多在杭嘉湖平原上长大的人而言,红烧羊肉绝不只是一道荤菜。它的香气,编织在了记忆深处的冬日经纬。
在海宁老家,它是席面上的“硬通货”。以前办红白喜事,只有高档体面的宴席才得一见,现在比较普遍。一般的是方块羊肉,更讲究的是“盘脚”,一只羊脚烧好后,正好放一盘,而羊蹄是翘楚,肉少而筋胶丰腴,形态又好,最是矜贵。
摆宴席烧红烧羊肉,以前的柴灶是用砖块专门搭的,后来是用铁皮桶改建的,现在则是一个钢铁定制的,可移动的,上面支一个大铁锅,下面用硬柴烧,是活火。烧制法是我国烹食文化中的传统经典技法。元末《易牙遗意》中记载了多种烧制的菜肴,其中就有“生烧猪羊肉法”。我们乡下烧红烧羊肉,未必看过这些菜谱,都是上一代传下来的,也都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
时代变迁,红烧羊肉从高高的礼坛走入寻常灶台。我家原来住在嘉兴建南公寓,小区的东北侧有个小店,专门卖新塍羊肉。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冬天时不时去买上几块全家品尝。
又到冬天了。周末回家,刚走到楼下,我就闻到了熟悉的红烧羊肉的香味。推开门,那香味愈发真切,带着红枣的甜、姜块的辛,以及酱油与冰糖在热力下交融成的醇厚焦香,丝丝缕缕,从厨房的门缝里钻出。母亲正在灶前守着,锅里咕嘟咕嘟,羊肉、萝卜与所有滋味正慢火滚作一团。燃气灶的火,终究不似记忆里乡下柴灶那般噼啪有声、烈焰灼灼;可锅中那一片由母亲耐心守候而成的、翻滚的醇浓,其温暖与劲道,早已胜过世上所有的火了。
一碗红烧羊肉的变迁,从凭票供应的年节滋味,到菜市场里从容挑选的日常食材;从需要节省着用的柴火与酱油,到灶台上琳琅满目的调料——这锅中风味的日渐丰厚与从容,便是最具体而细微的时代注脚。恰如一位先生所言,这滋味本身,便是“中国人生活史的一部分”。
在江南,这部生活史的风味,尤为绵长而富足。
江南人吃羊肉,历史悠远,这饮食习惯本身,就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北风南渐”。湖羊,如今杭嘉湖地区的绝对主角,其祖先正是宋室南渡时,随君臣百姓一同南迁的蒙古羊。这些北方的客旅,在太湖水网间“入乡随俗”,食桑叶,饮湖水,竟褪去了部分原有的膻悍,生出了肉质细嫩、膻味轻缓的江南品性。一块红烧羊肉里,便沉潜着民族迁徙与融合的宏大叙事。
因此,江南的红烧羊肉,自诞生起就带有一种融合的智慧与精致的追求。它不像北方草原上的手把肉那般粗犷豪迈,而是将北地的厚实,点化在了南方的文火与浓油赤酱之中。在湖州练市、嘉兴澉浦、苏州桃源,这道菜被演绎到了极致。
在澉浦,老食客们讲究的是“早烧”——清晨四五点,踱进小店,要一块羊肉,斟一二两烧酒,跷着腿慢饮细品,海阔天空地“讲白相”,寒意在微醺与肉香中消弭无形。这碗羊肉,暖的不只是身,更是那份从容不迫的生活意趣。“世上千百件美事,无非饮酒;天下第一等佳肴,当数羊肉。”苏东坡当年在杭州为官时,曾到海盐澉浦品尝红烧羊肉,对此大加赞赏并挥笔写下此联。
而我最怀念的,是前年在新市蹲点调研时,特意起早体验的“早酒”光景。春寒料峭,天光未亮,镇上的小馆已热气蒸腾。大铁锅里,红烧羊肉“咕嘟”作响,浓香霸道地充满窄街。我学着店里老顾客的样子,要了一份红烧羊肉面,还要了20元一瓶的白酒。我和“皮夹克”坐一桌,听他们用方言聊收成、谈厂房出租,所谓的“民情民意”,便不再是纸上的词汇,而成了真切可感的生活温度。
如今,这碗羊肉所承载的,早已超越了口腹之欲与岁时节令。它一头连着千年文脉与个人乡愁,另一头,则深深嵌入了当代乡村发展的经济肌理。
小时候,农家养羊多为副业,“主要为取皮和积肥”,羊肉甚至是副产品。我家当年大多养两只,多的时候有三四只。有一年,期待已久的日子终于来临,两头羊羔诞生,好可爱。母亲嘱我用箩筐背着去集镇的供销社卖羊皮。不多时,我拿着两张小羊皮换回来的十来元钱,背着剥了皮的羊羔回家。现在已记不清当时是揣着钱的喜悦,还是为小羊羔难过。
而今天,湖羊产业已是一条金光闪闪的富民链。在湖州的长兴吕山乡,湖羊种业已形成“保种—扩繁—加工—销售—文旅”五大产业集群,串联起5.6亿元的年产值。优质种羊远销新疆、甘肃、四川等西部地区。一碗红烧羊肉,背后是从育种、养殖、烹饪到文旅的整条产业链,是农民实实在在的增收致富路,吕山乡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去年达到了5.1万元。
当我再回想起广元那碗被“蒸干”的羊肉,遗憾之外,更生出一份理解与从容。地域的差异或许会让风味在途中折损,但文化的根脉与情感的纽带却愈发清晰。红烧羊肉在江南的演变,是从“礼”到“俗”,再从“俗”到“产”的生动历程。这道古老的菜肴,正温厚地推动着碗碟之外的世界。它的未来,不止于唇齿之间的丰饶。
无论走到哪里,冬日里,我胃里那份关于温暖的记忆,总会准确指向故乡灶台上那一锅酱红色的、酥烂香浓的羊肉。那是一封无需邮差的家书,上面写着千年风土,写着时代变迁,更写着每一个江南游子关于“家”和“根”的、永不冷却的体温。(作者为在职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