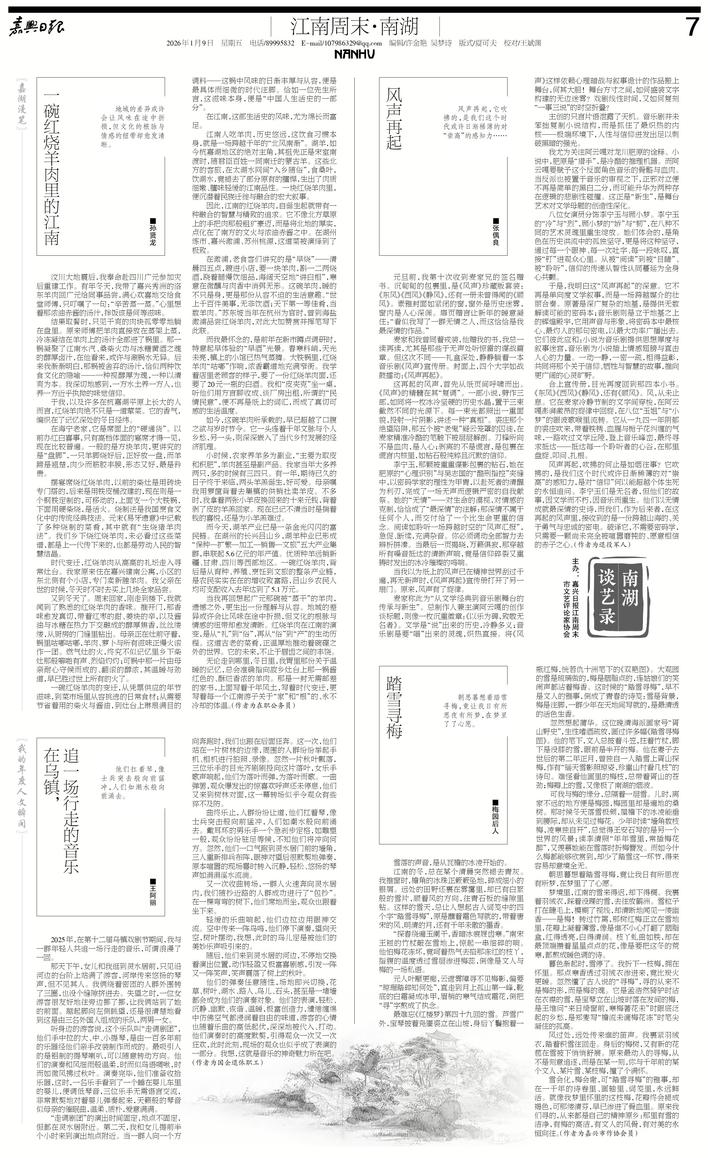■张偶良
元旦前,我第十次收到麦家兄的签名赠书。沉甸甸的包裹里,是《风声》珍藏版套装:《东风》《西风》《静风》,还有一册未曾得闻的《顺风》。素雅封面如紧闭的窗,窗外是历史迷雾,窗内是人心深渊。扉页赠言让新年的暖意凝住:“看似我写了一群无情之人,而这恰恰是我最深情的作品。”
麦家和我曾同着戎装,他赠我的书,我总一读再读,尤其是那些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谍战篇章。但这次不同——礼盒深处,静静躺着一本音乐剧《风声》宣传册。封面上,四个大字如战鼓擂动:《风声再起》。
这再起的风声,首先从纸页间呼啸而出。《风声》的精髓在其“复调”。一部小说,劈作三部,如同将一枚冰冷坚硬的历史水晶,置于三束截然不同的光源下。每一束光都照出一重面貌,投射一片阴影,讲述一种“真相”。裘庄那个绝望陷阱,那五个被“老鬼”疑云笼罩的囚徒,在麦家精准冷酷的笔触下被层层解剖。刀锋所向不是血肉,是人心;剥离的不是谎言,是包裹在谎言内核里,如钻石般纯粹且沉默的信仰。
李宁玉,那颗被重重谍影包裹的钻石,她在肥原的“心理识别”与吴志国的“酷刑指控”夹缝中,以密码学家的理性为甲胄,以赴死者的清醒为利刃,完成了一场无声而逻辑严密的自我献祭。她的“无情”——对生命的漠视,对情感的克制,恰恰成了“最深情”的注解:那深情不属于任何个人,而交付给了一个比生命更重的信念。阅读如聆听一场跨越时空的“风声汇报”,急促、断续,充满杂音。你必须调动全部智力去辨析拼凑。当最后一页揭晓,万籁俱寂,那穿越所有噪音抵达的清晰声响,竟是信仰碎裂又重铸时发出的冰冷璀璨的鸣响。
当我以为纸上的风声已在精神世界刮过千遍,再无新声时,《风声再起》宣传册打开了另一扇门。原来,风声有了旋律。
麦家称此为“从文学经典到音乐剧舞台的传承与新生”。总制作人兼主演阿云嘎的创作谈标题,则像一枚沉重徽章:《以乐为碑,致敬无名者》。文学是“说”出来的历史,冷静多义;音乐剧是要“唱”出来的灵魂,炽热直接。将《风声》这样依赖心理暗战与叙事诡计的作品搬上舞台,何其大胆!舞台方寸之间,如何盛装文字构建的无边迷雾?戏剧线性时间,又如何复刻“一事三说”的时空折叠?
主创的只言片语泄露了天机。音乐剧并未笨拙复制小说结构,而是抓住了最炽热的内核——极端环境下,人性与信仰迸发出足以刺破黑暗的强光。
我尤为关注阿云嘎对龙川肥原的诠释。小说中,肥原是“猎手”,是冷酷的推理机器。而阿云嘎要赋予这个反面角色音乐的骨骼与血肉。当反派也被置于音乐的审视之下,正邪对立便不再是简单的黑白二分,而可能升华为两种存在逻辑的悲剧性碰撞。这正是“新生”,是舞台艺术对文学母题的创造性深化。
八位女演员分饰李宁玉与顾小梦。李宁玉的“冷”与“烈”,顾小梦的“娇”与“韧”,在八种不同的艺术灵魂里重生绽放。她们体会的,是角色在历史洪流中的孤独坚守,更是将这种坚守,通过每一个眼神、每一次吐字、每一段咏叹,直接“钉”进观众心里。从被“阅读”到被“目睹”、被“聆听”,信仰的传递从智性认同蔓延为全身心共颤。
于是,我明白这“风声再起”的深意。它不再是单向度文学叙事,而是一场跨越媒介的壮丽合奏。原著是深广复杂的地基,是提供无数解读可能的密码本;音乐剧则是立于地基之上的辉煌殿宇,它用声音与形象,将密码本中最核心、最灼人的那句密电,以最大功率广播出去。它们彼此应和:小说为音乐剧提供思想厚度与叙事迷宫,音乐剧为小说插上情感翅膀与直击人心的力量。一动一静,一密一疏,相得益彰,共同将那个关于信仰、牺牲与智慧的故事,推向更广阔的心灵旷野。
合上宣传册,目光再度回到那四本小书。《东风》《西风》《静风》,还有《顺风》。风,从未止息。它在麦家冷静节制的文字间穿梭,在阿云嘎澎湃激昂的旋律中回旋,在八位“玉姐”与“小梦”的眼波歌喉里流转。它从一九四一年阴郁的裘庄吹来,带着铁锈、血腥与栀子花纠缠的气味,一路吹过文学丘陵,登上音乐峰峦,最终寻求抵达——抵达每一个聆听者的心谷,在那里盘旋、叩问、扎根。
风声再起,吹拂的何止是如烟往事?它吹拂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或许日渐稀薄的对“崇高”的感知力,是对“信仰”何以能超越个体生死的永恒追问。李宁玉们是无名者,但他们的故事,因文学而不朽,因音乐而重生。他们以无情成就最深情的史诗,而我们,作为后来者,在这再起的风声里,接收到的是一份跨越山海的、关于勇气与忠诚的密电。破译它,不需要密码学,只需要一颗尚未完全被喧嚣磨钝的、愿意相信的赤子之心。(作者为退役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