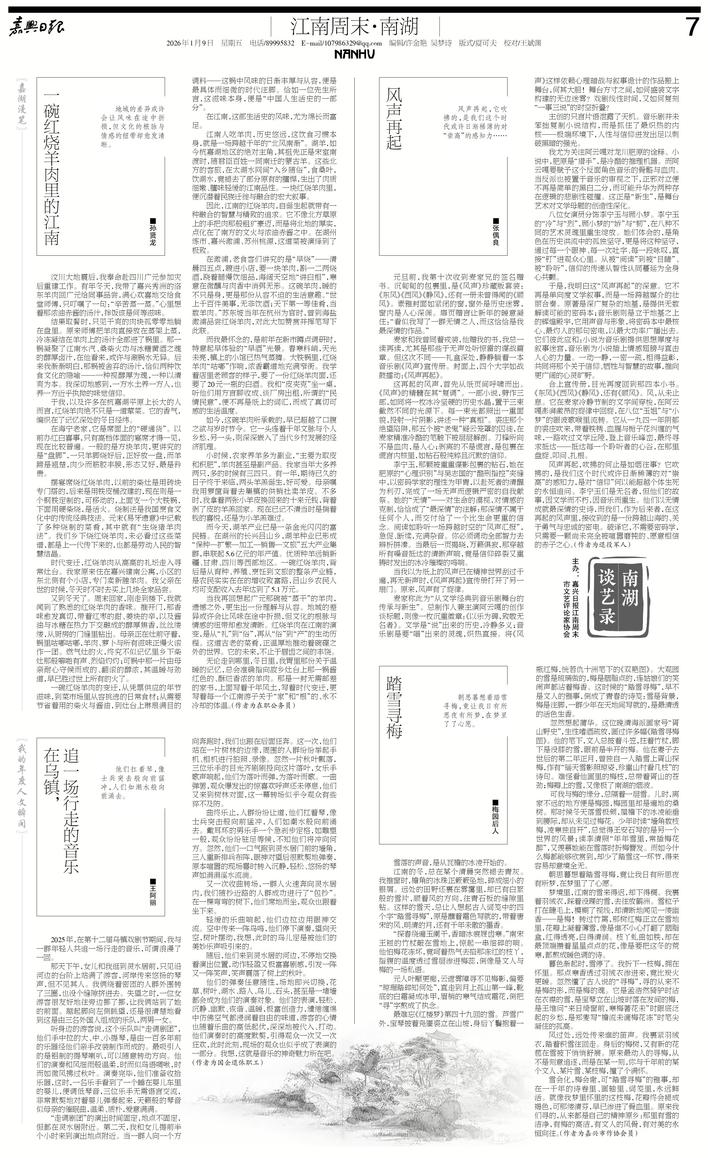■梅园后人
雪落的声音,是从瓦檐的冰凌开始的。
江南的冬,总在某个清晨突然褪去青灰。我推窗时,檐角的冰珠正簌簌坠地,碎成细小的银屑。远处的田野还裹在雾霭里,却已有白絮般的雪片,顺着风的方向,往青石板的缝隙里钻。这样的雪天,总让人想起古人词笺中的四个字“踏雪寻梅”,原是蘸着霜色写就的,带着唐宋的风、明清的月,还有千年未散的墨香。
“探春绕遍玉阑干,香暗冰痕屐齿寒。”南宋王镃的竹杖敲在雪地上,惊起一串细碎的响。他怕梅花冻坏,竟呵着热气去掐那冻红的枝丫,指腹的温度透过雪层渗进梅蕊,倒像是文人与梅的一场私语。
元人叶颙更痴,云遮雾障寻不见梅影,偏要“琼琚踏碎知何处”,直走到月上孤山第一峰,靴底的白霜凝成冰甲,眉梢的寒气结成霜花,倒把“寻”字熬成了执念。
最难忘《红楼梦》第四十九回的雪。芦雪广外,宝琴披着凫靥裘立在山坡,身后丫鬟抱着一瓶红梅,恍若仇十洲笔下的《双艳图》。大观园的雪是琉璃做的,梅是胭脂点的,连姑娘们的笑闹声都沾着梅香。这时候的“踏雪寻梅”,早不是文人的雅事,倒成了青春的诗笺:雪是背景,梅是注脚,一群少年在天地间写就的,是最清透的活色生香。
忽然想起蒲华。这位晚清海派画家号“胥山野史”,生性嗜酒疏放,画过许多幅《踏雪寻梅图》。他的笔下,文人总披着斗笠,拄着竹杖,脚下是没膝的雪,眼前是半开的梅。他在妻子去世后的第二年正月,曾独自一人踏雪上胥山探梅,作有“瑶天雪影照琼姿,珍重山村看几枝”的诗句。难怪看他画里的梅枝,总带着胥山的苍劲;梅瓣上的雪,又像极了南湖的烟波。
可我与梅的缘分,总隔着一层雪。儿时,离家不远的地方便是梅园,梅园里却是遍地的桑树。那时候冬天落雪极频,屋檐下的冰凌能垂到腰际,却从未见过梅花。少年时读“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总觉得王安石写的是另一个世界的风景;读李清照“年年雪里,常插梅花醉”,又羡慕她能在雪落时折梅簪发。而如今什么梅都能够欣赏到,却少了踏雪这一环节,得来容易却意境全无。
朝思暮想着踏雪寻梅,竟让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梦里了了心愿。
梦境里,江南的雪来得迟,却下得稠。我裹着羽绒衣,踩着没踝的雪,去往放鹤洲。雪粒子打在睫毛上,模糊了视线,却清晰地闻见一缕幽香——是梅!转过竹篱,那树红梅正立在雪地里,花瓣上凝着薄雪,像是谁不小心打翻了胭脂盒,红得透亮,白得清润。枝丫虬曲如铁,却在最顶端攒着星星点点的花,像是要把这冬的荒寒,都熬成暖色调的诗。
暮色渐起时,雪停了。我折下一枝梅,拥在怀里。那点寒香透过羽绒衣渗进来,竟比炭火更暖。忽然懂了古人说的“寻梅”,寻的从来不是梅的形,而是梅的魂。它是孟浩然骑驴时沾在衣襟的雪,是宝琴立在山坡时落在发间的梅,是王维问“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时眼底泛起的乡愁,是郑燮写“檐流未滴梅花冻”时笔尖凝住的孤高。
风过处,远处传来谁的笛声。我裹紧羽绒衣,踏着积雪往回走。身后的梅树,又有新的花苞在雪被下悄悄舒展。原来最动人的寻梅,从不是刻意追逐,而是在某一刻,你与千年前的某个文人、某片雪、某枝梅,撞了个满怀。
雪会化,梅会谢,可“踏雪寻梅”的雅事,却在一千年的诗卷里、画轴里、词笺里,永远鲜活。就像我梦里怀里的这枝梅,花瓣终会褪成褐色,可那缕清芬,早已渗进了骨血里。原来我们寻的,从来都是自己的精神原乡:那里有雪的洁净,有梅的高洁,有文人的风骨,有对美的永恒向往。(作者为嘉兴市作协会员)